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的“融摄”精神一向为国人所称道,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具有宽阔的文化胸怀的有力证据。由此,国人又常常因此而联想到西方的“异教徒”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长达二百余年旷日持久的“十字军东征”,对西方人于信仰问题的固执并为此大动干戈,或嗤之以鼻,或一笑了之。但是,从文化接受的形态方面考察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接受状况,则由一个侧面深刻反映出中国佛子的对时代和主流文化的几乎出于本能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其实质是媚俗顺世。因为,其中所发生的事实已超越了文化交流现象中必然产生的融合互摄,也非比较宗教学意义上的教理嫁接和教规移植,而是中华文化形态对拥有异己性质的印度文化形态的无视其文化特质的强制改造,也是佛子们对本土文化形态的无原则苟合趋同。这一问题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即相伴而至。其正面的功效是推动并促进和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使佛教这个纯属异质的宗教文化得以在儒学一统天下的中国找到其适合的生存土壤。
但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嬗变的过程中,也随之串味变质,当儒释道三家合一之风盛行时,正统的印度佛法面对强大的中国本土风俗和主流思想体系,则只能发“梅熟已过南岭雨,橘酸空待洞庭霜”之感叹了。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玄奘大师一生即在为寻觅其真正印度佛学的“橘味”而不懈努力,但国人却久尝“枳味”,而对“橘味”兴趣索然,于是,在为玄奘大师送上最美妙的颂词之后,将他的思想学说束之高阁,自赵宋以降,直至清末,寺院以经忏适应民俗,僧众以佛事迎合民众。即使论禅谈道,也流于文字般若,与文人的吟花弄雪般的无病呻吟同出一辙,缺乏宗教所应有的人文关怀,更无从谈宗教所必须拥有的神圣品质和终极关怀!
有幸的是,对此佛法日益式微的现象,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和佛教居士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予以具体分析,从源头上寻找解决的途径,即由对佛学基本文本的校勘和辨析入手,旨在还原释尊真意,阐述佛法基本原理,并从历史的纵向上和教理教义教规本身现状的横向上总结千余年中国佛教流弊。其中,尤以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支那内学院派居士和学者贡献最著。特别是吕澂先生,他曾经就中国佛教所存在的导致佛法宗旨串味弊端,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抨击。其在《佛法与世间》的演讲之附识中指出:“今之谈佛法有三大病,若不及时对治,终必不可救药。三病者何?一曰泥迹,专讲婆诃苦恼、生死可畏一套话头,引人厌世躲闪,此从小乘出,却毫未学得小乘之严肃深刻精神,只剩有浑身的自私自利解数。此为一大病。次曰蹈空,专唱高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说得一片响,完全不着边际,反倒转来以涅槃菩提将就生死烦恼,由此引人向浮泛空虚,真同方广道人,于佛法却一无所得。此又为一大病。三曰纯任知解,无论说生道死,谈空论有,概从知解上理会,只图说得顺口动听,不管于自身受用如何,不问于他人利益如何,更不理会于此人世如何衔接得上,结果一场空话,竟与人生漠不关心。此又为一大病。”[1]此分析持之有故,立之有据,凡正视中国佛教历史,又有人格勇气直面现实者,当认可吕澂先生鞭辟入里的分析。
吕澂先生毕生的佛学研究,其主旨在于为佛法正本清源。他的佛学贡献不仅表现在对佛学文本的校勘、伪经的辨析,以及对印度和中国、西藏佛学体系及其历史沿革的研究和整理方面,也不仅表现在他几十年如一日,以其深厚的佛学造诣结合天才般的语言功力,校勘出版了在学界和教界影响甚巨的《藏要》,编撰了《中华大藏经》的目录。笔者以为,他的学术活动以基础性的文本清理辨正为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佛学文本的清理辨正,发掘、寻觅已被历史长河所堙灭的释尊真意。因此,他通过自己所写的系列著作,表达了佛陀的本意,在貌似枯燥的学术论述中,展现了佛陀的本怀。其中,分别以《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为题的三篇论文,同时又以《佛法与世间》为题的演讲作辅翼,构成了佛学基本问题系列著作,虽在其整个著作体系中的分量并不重,但这三篇论文确乎是独步佛坛的孤明首发之力作。《正觉与出离》阐述了佛法修学的根本目的和途径,《缘起与实相》阐述了佛法的基本教理和学术宗旨,《观行与转依》阐述了佛法的基本修学方法和修学过程。所以,吕澂先生将上述三篇论文均冠以“佛学基本问题”的副题。其实,正如众所周知的是,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本非佛教入门教课本一样,以“佛学基本问题”为副题的上述三篇论文,也决非佛学基础知识读本,而是吕澂先生对佛学的基本、普遍、重要的教理、观念的精心整理和阐发,在吕澂先生的佛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代表意义。因此,本文仅在吕澂先生博大精深的佛学学术体系中,藉此三篇论文暨《佛法与世间》演讲所涉及的范围,阐发吕澂先生的佛学思想之内涵。
一、正觉并非难测,出离决非玄虚
《正觉与出离》一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佛学》杂志1953年第十二期上。是吕澂先生关于佛学基本问题的论题之一。故该文所涉及的是佛教最为基本的问题修学的根本目的和途径。
所谓正觉,是佛法的一个常新命题。正觉是释尊最初所弘传的“八正道”之总称[2]。一般对于正觉的解释是,以正智觉悟正理。正觉又是指修行所达到的果位——梵语谓三藐三菩提,经中阐述到:“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3]佛教中,又往往将释尊于菩提树下金刚座上真实准确觉悟缘起法,证得解脱名为正觉,“即便持草往诣觉树,到已布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要不解坐至得漏尽,我便不解坐至得漏尽。我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便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便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生知生见,定道品法,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我初觉无上正尽觉。”[4]慈恩宗高僧、玄奘大师高足窥基师在其所著之《法华经玄赞》卷二中对正觉的性质作了阐述:“一无上觉是总也,即显菩提清净法界;二正觉简外道邪觉故;三等觉简二乘但了生空偏觉故;四又正觉简菩萨。菩萨因觉未满果位,非正觉故。”[5]唐代华严宗的实际创始者法藏大师在其传世名著《华严经探玄记》卷二中,又依五教之理,别开生面地论述了正觉的不同层次:“一约小乘。以生身佛于此树下三十四心初成正觉同诸罗汉实成非化。二约大乘。八相化身示现于此初成正觉。三约报身。十地行满无间道后果现圆明名初成正觉。四约法身。谓创得了因最初圆现。故曰初成。此上大乘并无初之初。五约十佛。谓遍一切因陀罗网无边世界。念念之中皆初初成佛。具足主伴。尽三世间。是故此即具摄前后无量劫初也。此中正唯第五兼摄前四。准可知。”[6]即谓初成正觉,在小乘是释迦生身之实成,在始教是八相化身的示现,在终教是十地行满的报身,在顿教是法身初成,在圆教是遍因陀罗网无边世界,念念初初成正觉。
而所谓出离,则是针对人类社会现状所作的,为佛法所特有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对于世间的一种否定式表达。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佛法中的出离之名相,特指超脱生死轮回之苦而成就佛道。经中有言:“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7]经中又说:“若有众生乐出离,应当发起菩提心。”[8]上述经文所表达的出离之主旨,是基于人生是在逼恼苦迫中煎熬的价值判断,乃将众生分别由欲望、色相、情识所构成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视作牢狱火窟,离脱惑业之系缚,名为出离。《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中,更进一步对出离的的目标予以分析总结,认为出离的目标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为出离三恶趣而趋向人天善趣;一为出离轮回生死而趋向三菩提。此外,法藏法师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三中认为,声闻修道者有渐出离、顿出离之别:“又进修道人有其二种,一渐出离,断欲界九品中前六品,尽得一来果。断九品,尽得不还果,断上二界,尽得阿罗汉果。二顿出离者,谓得初果已。即顿断三界,渐除九品,即得阿罗汉果,更无余果。”[9]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论中,“出离”一词还常与“出要”混用。如《十地经论·菩萨离垢地》卷二中说:“是诸有情随贪嗔痴因缘而转,常以种种烦恼火焰之所烧爇,不复访求出要方便。”[10]又《长阿含经·三明经》卷十六说:“共相是非汝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11]《摩诃止观》卷七中也说到:“眠不安席,食不甘哺。如救頭然。白駒烏免日夜奔競。以求出要。”[12]
由上述的论述可见,佛学界给予正觉与出离的问题以一贯的关注,似乎这是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吕澂先生在《正觉与出离》中,开宗明义将正觉与出离的问题,视作为事关人生趋向的重大佛学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了‘正觉与出离’的一个题目来,是要分析、说明佛家对于人生趋向有怎样的看法和主张。”[13]明确了正觉与出离是一涉及佛法对于人生趋向的基本态度和主张的重要范畴。佛法的人生态度,来自于佛法对于人生的基本价值判断。“人生是苦”是佛法对于世间的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基本价值判断,也是佛法正觉的出发点。对于人身之生老病死的切身之感,是释尊创觉佛法和笃行修学实践的原始动机,也是释尊无量慈悲开示佛法的现实因缘。因此,拨开被历代佛子渲染得神乎其神,遮蔽于正觉与出离境界上的神秘面纱,还其导引众生人生趋向的本来面目,是吕澂先生的立论之基点。
人生的趋向可谓是世态缤纷。但以佛法的分析,无非是两种,一为流沦苦迫而无着落的世间凡夫人生,一为解除苦迫系缚的圣道人生。吕澂先生明确指出:“这种始终回旋、起伏、不得着落的人生,佛家谓之‘流转’。佛家对于流转的解释,有时比较宽泛。这里只就人的本位而言。要是人们真正找到了人生欠缺的原因,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这在形式上看来,对流转的生活是取相反的趋势,并还有破坏它、变革它的意义,所以谓之‘还灭’。由此,佛家区别人生趋向为两途:一是流转的,不合理的,不应当的;一是还灭的,合理的,应当的。所有人生行事,都可用这种标准来分为两个系列。”[14]佛法的学术体系,即按此两系列架构,佛法的修学也依此两系列展开。但是,佛法在世间的流行中,由于佛弟子各自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对世事的感受、对佛陀甚深旨意的理解上的差异,导致了对佛法所指引的由“流转”向“还灭”的转化之路该如何走,该如何实际地、依照佛旨看待人生的观点和方法上的迥异。主要表现在佛陀后时代先后出现的印度两大佛学思潮,即首先表现为以迦叶为代表的上座部与以阿难为领军的大众部之间的争论交锋,以后又衍演为印度佛教史上蔚为壮观的声闻乘(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睿智撞击。
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虽都承诺自己系继承佛陀旨意,但大乘与小乘相互间在正觉与出离问题上的主张之差异,是非常突出而关键的。吕澂先生深刻地指出:声闻乘“他们以为人生欠缺、痛苦的原因,即在人生的本质上。分析人生,因的方面是业惑,果的方面即是苦。要去掉苦果,应该断业,灭惑,不使再生。但业是种种行为,惑是种种烦恼,业惑之生起,在人事上随时随地几乎无法避免,要断灭它们,很容易走向禁欲一途,企图由隐遁的方式摆脱纠缠,而此种消极办法又必然远离社会而变成自私、自利。其结果虽不能说完全落空,但终非究竟解决。因为他们的出离世间竟是舍弃世间,本来要对人生有所改善,反而取消了人生,所以说它是不彻底、不究竟的。”[15]吕澂先生又阐述到:“在印度,佛家以外的学派也很多带着这样倾向,一般人受着薰陶,对于声闻乘的说法就很易予以接受,因而使它流行了很久。后来佛学传到中国,尽管那时菩萨乘的势力已极发展,主要的义学也都以菩萨乘为依据,但实际上仍离不掉声闻乘的作风。这给与佛学的流行以很不好的影响,向来中国佛学受到外来的批评、攻击,即是集中在这方面的。”[16]在此,吕澂先生所指应该是小乘佛教所带给中国佛教的过分关注个体的“生死果报”话头,将佛教蜕化为消极遁世、拘泥死板的教条的弊端。
历史上的佛教僧团确实曾经走向过禁欲一途。辨证地看,在印度社会中笃行不移的禁欲被转化成“自了汉”的修行实践,虽与佛旨相悖,然而确实引发了修行的严谨风尚。在中国佛教界,禁欲之修行始终未成为主流,佛子们虽崇敬笃行者的精进刻苦,也向往能够“自了”,其自私自利之心决非亚于印度民众,但农业文明所熏染出来的实用主义和崇尚实在的风尚,使消极遁世遁俗的印度小乘佛教在中土难有生存之基。故在中国佛教中,真正笃行禁欲之“苦修”之道者,实为寥若晨星。所以,吕澂先生对中国佛教界普遍存在的崇尚浮夸玄谈、忽视笃行实践、颟顸佛陀本意的风气,曾在其《佛法与世间》一文的附识中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见前所引述——笔者)。
吕澂先生《正觉与出离》一文中,揭示了声闻乘佛法在正觉、出离问题上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大乘佛法于正觉和出离问题上前后一贯的特点:即,一、大乘佛法探究人生问题,是从全面而非个体的角度出发,因此,大乘佛法虽如声闻乘一样强调“业”之作用,但更为强调的是“共业”之功效,即注重众生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与声闻乘仅注重个体的人生,其眼界的宽狭自不待评述;二、大乘佛法虽与声闻乘佛法一样注重折伏烦恼,但认为烦恼产生于有情与世间的关系,人生无法避开其所面对的世间一切而独立存在,所以消极避世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包括悟道在内的一切修行实践,都必须、而且只能在现实的世间之中进行,在烦恼中与烦恼搏斗,以达到最终转化烦恼为无烦恼。这一观点体现了大乘积极入世、大隐于世的积极的折伏烦恼的态度和方法;三、厌弃苦迫,是佛法一贯的观点。大乘虽也同样厌弃苦,但其与声闻乘境界上的差别在于,从积极的厌弃中更进而产生无尽的悲心,即恻怆他人之苦而欲救拔的心理。自觉苦而他人却不觉,自己能解除痛苦而别人却不能,由此油然而生不忍之恻隐,即为悲心的开端;四、大乘佛法与声闻乘佛法,在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上可谓迥然相反,大乘佛法并不消极避世,而是积极理解现实世界的实际。所以表现出遵循“依义不依语”的原则,对待佛法及佛陀话语的灵活的、契机契理的运用,以求契合实际而发生真正的智慧,达到概念与实际的统一认识;五、大乘佛法的悲心和智慧与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最为突出的是关注印度社会所存在的种姓之不平等的弊端,适时契理契机地唱响了“一切众生平等”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佛陀本旨,确认众生在人格上和宗教信仰上的平等性。而此点又恰恰是声闻乘佛教所不予关心注目的。[17]
由上述五方面可见,大乘佛教自始至终将正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将出离建立在与世间的“俱而不染,即相涉而不相应”[18]的关系上。与世间不相涉,则无法汲取世间的养分,无法扎根于现实的社会,佛教既会成为无本之木,或与世人凡夫无涉的苍穹玄音,佛法的生命力必将枯竭,更无从谈及救拔众生于苦海的济世之功能的发挥;但与世间相应,则无法超脱于世间的言说之构想、染相之取著、业惑之系缚。所以,《宝积经》说佛陀如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于淤泥,充分说明了佛法与世间“相涉而不相应”的关系,非扎根于世间淤泥,莲花则成无本之木,非出于世间淤泥,莲花则成有染之物。
大乘佛法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龙树、提婆为代表的中观学派,以及继起的以无著、世亲为代表的瑜伽学派。印度佛学历史上,两大学派的争论辩驳唱响了中后期佛教的主旋律,其融合交涉虽不乏有心者,但毕竟还是凤毛麟角。其中,我国留学那烂陀寺的玄奘大师是融合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成员。其所著的《会宗论》对架构两大学派的教理教义体系之间的联系,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吕澂先生在其作于1964年6月,而未选入自己选集的《玄奘与印度佛学》一文中,特别指出:“他以独到的见解对印度佛学作出贡献,则主要在于他学成将返之时(约当公元六四一年),连续用梵文写出了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19]。“当玄奘到达那烂陀时,寺中早已形成了两派对峙。玄奘师事的戒贤是瑜伽行派护法(约五三○——五六一年)的嫡传,而持反对议论的师子光则属于中观派清辨一系。他们各趋极端的见解,在那烂陀似已无人再作调和之想了。但是玄奘到来,独提出主张予以会通。”[20]玄奘大师的会通,据吕澂先生结合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所附玄奘小传等资料所进行的分析,玄奘大师当从“应舍执著空有两边,领悟大乘不二中道”[21]的护法师观点出发,由中道理论会通瑜伽。但是,中观与瑜伽之间的分歧,以及中观、瑜伽学派内部的分歧是印度佛学历史上的史实,玄奘大师的会通,在印度大乘两大学派中并未一劳永逸地消除分歧。笔者以为,中观、瑜伽学派的分歧之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学术出发基点以及学术方法上的差异。中观学说以探究诸法实相为其宗旨,注重于本体论上的本质性把握;而瑜伽学说以追溯万法之相为其要务,立足于认识论上的精微分析。所以,两者之间虽无法就其学术基点和学术旨趣、方法进行融合,但两者都与佛旨相契合,故其分歧点也并无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
吕澂先生《正觉与出离》文中,对中观学和瑜伽学的特点,有着深刻的阐述和精到的把握。并由此揭开了蒙在正觉、出离上的种种迷雾。其实,正觉并非难测,出离亦非玄虚。
中观学的特色,正如吕澂先生所深刻指出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现象,如没有真正智慧,就不会得其实在,由此发生颠倒分别、无益戏论(执着),而招致人生的无穷痛苦。但这种迷执可以从根本上解除,最重要的是体会一切事物现象实际和那些执着无干,并不像分别戏论那一回事,也就是没有分别戏论所构画的那样实体,这谓之‘无自性’,谓之‘空’。在形式上,这无异把分别戏论给与现象的染污去掉了,而见着它原来的寂静面目,所以谓之‘法性本寂’”。[22]这即反映了中观学的学术特色,也是中观学对正觉最为生动的阐述。对现实世间的“颠倒分别”和“无益戏论”的勘破,即为正觉,而由此达到还其包括有情在内的诸法的本来面目,即进入“法性本寂”的境界,即是出离。此出离以正觉为前提,正觉以出离为目的,而正觉须即世而得,故龙树中观学的特色即在于首倡“世间与涅槃,无有少分别”,“涅槃与世间,亦无少分别”。[23]确立了世间与涅槃的不即不离,虽互为迥异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吕澂先生精确地将其归纳为“即世而出世”之特点。
瑜伽学在学术风格上与中观学有着诸多的差别。依照吕澂先生之观点,中观学高扬世间实际即为涅槃,瑜伽行派的唯识学则贯通世间众生的实践与佛法诸法实相之理的相应。龙树系佛学体系确实有诸多内容未得充分发挥。而无著世亲则发挥为泱泱大观的瑜伽行,也系学术完善之需,更为众生由佛法而求实证悟道的需要所致。无著世亲以《阿毗达磨经》和《瑜伽师地论》等重要教典为依据,运用“优波提舍”即论议,以及“阿毗达磨”即对法的表述体裁,批判性地解释佛说。依据于此,在其精致博大的佛学体系中引进了“瑜伽师地”的位次,“无住涅槃”的行,“转依”的果等新的范畴,构建了认识的异熟、思量、了别三“能变”、以与生俱有的“藏识”为“所知依”,诸法由世间到出离的三性三无性的转依理论体系。吕澂先生特别指出:“其中尤以‘转依’一个范畴,用作‘解脱’的代替语,更能显出解脱的积极意义。”[24]故吕澂先生将无著世亲系的瑜伽体系的正觉出离之特点,精到地称为“转世而出世”。
最后,吕澂先生分析了佛教在其发展历史上对佛陀旨意的种种误解。确实,对于佛法的误解,是引发佛教诸弊端和极端性倾向的重要因素。佛法流布世间,其主要的误解有:
一、狭隘地将佛法的人生观理解为生死观。或一味追求“死”之外在的神奇形相,或一味迎合国人风俗,大做“死”后的经忏形式,以求所谓的“了生脱死”,佛教因而背上“死人宗教”的歪名。却不知“了生”乃是对于人生的了悟,洞彻,即正觉,而“脱死”乃是从对以“死”为代表的烦恼、所知及业障中挣脱,即出离。依吕澂先生的说法是,从不实在的、虚妄的“言说之构想,染相之取著,业惑之系缚”[25]中解脱出来。佛法的“无我”说,已经根本否定了实在的“我”之自体的实存性和可把握性,此定论也是通三世十方的。既然“无我”,则不存在实在的“出离”也在其意义之中。
二、误认佛法是一种旨在否定人生价值的消极的宗教体系。佛陀有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以生灭故,彼寂为乐”。[26]由此推断,认为人有生即苦,免苦除非不生,此说仅理会到声闻乘之知见,显然是欠全面的。实际上,佛陀的原旨在于,只要遣除生灭法中与能生种种惑业的欲取相联系之诸行,即从以欲取为中枢的一切具有烦恼障和所知障作用的生灭法的覆灭并趋于寂静,以此构成涅槃境界。佛法讲诸行无常但不否定诸行的必要性,佛法讲诸法皆空旨在说明对于一切法的不可执著,但凡对于诸法的执著和对于诸行的拘泥,则必无从出离,因其对行与法的认识是非正觉。由此可见,佛法对于人生苦之探源,对人生问题的彻底解决,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与其说佛法旨在否定人生,到不如说佛法意在改造人生,完善人生。
三、误认为菩萨乘所指示的人生归宿与声闻乘并无二致。菩萨乘似乎肯定世间,但是并未相应地丰富其解脱的内涵,因此其追求解脱的范围也未得到应有的扩充。虽菩萨乘首倡“不为己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最终还是归于对人生的否定。其实,菩萨乘所指的解脱涅槃的内涵已经包含着般若、法身和解脱之三德。为解脱涅槃所作所行的,不仅是解除一切苦恼,还需累积一切功德,由此构成法身境界。消除自他之间的沟壑,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功德的累积正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消化私我为大我,构筑涅槃法身。由此因缘,此解脱涅槃境界具足常乐我净之特征,符合人生基本要求。这并非从一己利害之立场出发的声闻乘修行解脱观所能够理解。这种解脱涅槃观也不能够归于对于人生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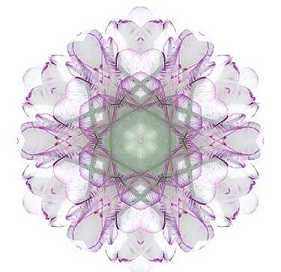
关照人类现状,直面人间疾苦,破解人生难题,是佛陀的本怀,而崇敬佛陀品格,折服佛法睿智,笃遵佛门行持,是佛子的情怀。沟通佛陀本怀与佛子情怀之间的心要,则是对正觉的趋同和对出离的实践。在此,关键的是把握正觉与出离,以及所牵涉到的世间与出世间的联系。无怪乎吕澂先生将《正觉与出离》一文作为佛教基本问题之首,予以郑重提出,并在论文的最后明确:正觉与出离的问题“牵涉到世出世的问题,依着菩萨乘的践行,是要投身于世间,渗透于世间,而求世间本质上的变革,并无脱离世间生活的说法;前面所提到的‘转世而出世’,正是这个意思。”[27]其对众生学以至用的期许,可谓古道热肠,天地可鉴。
二、缘起当悟深意,实相务须厘清
《缘起与实相》一文,最初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发表于《现代佛学》杂志1954年第五、六期上,是吕澂先生关于佛学基本问题的论题之二。《缘起与实相》一文以佛法的基本教理缘起说与实相说为其论述对象。厘清了佛教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其缘起与实相理论上的脉络。
缘起说是佛法教义体系的中心观念。从语义上说,缘起即为“依缘而起”之义。依缘即为依托于一定的条件、因素;起则指发生、升起。因此,缘起就是依托于各种条件而产生诸法事相,也即阐述诸法相互依存关系的原理。佛陀曾经以十分朴素而又形象的语言描绘过诸法缘起的事实,这即是在诸《阿含》中频频出现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诸法的无常性显示其生息不已,但变化却不无规律,而是一定条件下的变化迁异,其实质性的法则就是缘起。缘起本身与如来的出世与否都无关系,就如万有引力定律与牛顿出世与否没有关系一样,但是此根本性的法则,却是由释尊所发现并开示于芸芸众生的,故印顺导师曾一再赞叹佛是佛法的“创觉”者,此创觉者与我们的差别,比牛顿与学习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中学生之间的差别更大。佛说缘起,《初分说经卷下》说为:“若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是生灭因缘,佛大沙门说。”[28]而有部的《毗奈耶出家事》卷二则译为:“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29]缘起说的意义在于说明一切因条件而生的诸法事相,必以条件的消失而归于灭。缘起说是对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的法印说的本质性的阐述。因此,如果说法印说是佛教的根本特征,则缘起说即佛教的根本教义。我们据此可将缘起说视作为佛法。
原始经典中常见的“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缘起”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等句式,一再表明了缘起说在佛法中的中心地位。而此中心地位的确立,与佛陀那博大的宗教家的胸怀有着密切的联系。佛陀不是科学家,他所最为关注的并非世间万法的活动变迁规律,而是众生的疾苦,是对人生终极关怀的透视,是对现实众生的人文关怀。由此,他所注重的是探究众生沉浸苦海而不觉、迷失惑业而不悟的严峻现实,寻究其因。据此我们可断定,佛陀的缘起说,与西方学界的逻辑学及因果论说相比较,更多地具有终极性、人文性的因素。他的缘起说,自始至终与四谛说、法印说、解脱说、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等教理的发微密切相关,而万法的因果规律的发现,则是后来者的发挥所致,并非他老人家的本怀和注意点。佛教中缘起说与四谛说、法印说的关系,日本佛学家水野弘元在其所著的《佛教要语的基础知识》中,简单明确地以下表作了总结:
缘起说 缘起略说 四法印
一般缘起观念 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时间的前后) 诸行无常
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空间的、论理的) 诸法无我
业感缘起(四谛法印) 缘无明有行──┐┌苦(果)┐缘行有识……├流转┤│缘生故老死等…│└集(因)┘苦蕴聚生───┘ 一切行苦
无明灭故行灭─┐┌灭(果)┐行灭故识灭……├还灭┤│生灭故老死等…│└道(因)┘一切苦蕴灭──┘ 涅槃寂静
反观佛教的发展史,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及东南亚的佛教,都是以缘起说为中心思想。故如能充分了解缘起说,即可了解佛教。缘起说不仅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充分诠释了“众生皆苦,离苦得寂”的核心观念;同时,缘起说也是佛法与其他宗教、哲学的分水岭,体现了佛教独有的特征,构成传统中国佛教思想两大系统的重要一极。
中国传统佛教思想,由缘起论和实相论所组成的。二者的区别是:缘起论探究的是诸法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实相论则探究诸法的本质特性。但是,实相论所探究的诸法的本质特性,实际上是建立在缘起论所探究的诸法在时空上、精神中的相互依存联系之基础上的,是缘起说所显现的诸法本质特性,是缘起说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此意义而言,一切佛学均可涵盖于缘起说之中。龙树菩萨所倡导的“缘起性空”的中观理念,十分明确而又清晰地显示了实相说与缘起说的逻辑关系。吕澂先生也是基于此,才将缘起与实相予以一并考察研究的。
自佛陀创觉佛法以来,依佛子们的根机,及学说随时代的变迁,其关注的焦点和视角的差异,产生了多种缘起论:除原始佛教和以后发展的说一切有部等坚持以业力作用的视角所阐述的业感缘起论外,在大乘佛法中,以龙树提婆为代表的中观学主张推究“诸法实相”的实相说,但也同时倡导其独具特色的“八不缘起”说;而以无著世亲为代表的瑜伽行派则以阿赖耶识的异熟转依的视角,立赖耶缘起说;以后又发展到中后期大乘佛法,以真常唯心说为其特色,立如来藏缘起论(或称为真如缘起论);最后,在秘密大乘佛教时期,立六大缘起说。这即印度佛学在本土的流变。而在中国佛学的发展历程中,除三论宗和慈恩宗、真言宗分别承继印度佛学原旨外,又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华严宗之法界缘起说、天台宗之法性缘起说、禅宗之自心缘起说等等,但其缘起说与实相说的已经紧密地相联接和贯通。
吕澂先生的《缘起与实相》一文,开宗明义即说明了实相说与缘起说的关系:“关于实相的理论,在佛家始终与因果规律分不开来。他们自称其说为‘内明’,而用以区别其他学说的特点,就在于正确地说明因果,并配合着‘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业报法则。因此,佛家的实相说常和缘起说连在一起,主要从缘起的现象上见出真实的意义即实相。”[30]充分表明,实相的判断和把握,并非缘于冥想或随意猜测,而是对缘起现象的深刻洞察。他的观点含义极其深刻。笔者认为,至少向世人透露了三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一是,诸法实相是以诸法的缘起现象为前提的,实相无非是缘起所体现诸法的本质特性。因此,任何人的悟道和解脱,须以对缘起法则的领悟和践行为其基础;二是,佛法的证悟解脱之理与对世间诸法的现象的了解悟解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佛教的在世性、普世性和现实性,是佛法应有之义;三是,信解行证中,只有缘起法的现象表现,即缘生诸法,才能够引起众生的信解行,而实相法必须经过由缘生现象的理解指引,从而产生对缘起甚深法的实证,再进而对实相法的确认这样的多重阶段。因此,一切笃实的修行必然的应当而且只能够建立在对佛法教义的学习理解领悟的基础之上。轻视、贬低甚至抛弃佛法教义的作为,无论其是否意在强调修行的重要性,都是对于佛法修行基础的动摇,是架空佛法修行证悟的基石。
吕澂先生根据佛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依照其理论外延的由狭隘至广阔,将佛法缘起说分为,一、强调人生由业力作用推动的业感缘起说;二、推广至由众生与所处的客观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的受用缘起说;三、从对一切法与众生的互动关系考察的,宇宙万法间作用的分别自性缘起说。并认为:“具备了这三种学说,就构成佛家缘起理论的整然体系。”[31]这一分法,与其他佛教大家的分法不同,有其自身独特的学术魅力。既然缘起说旨在描绘阐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法则,则其所包括范围的广阔程度,确实是衡量缘起说、分析缘起说的重要标志。
进一步,吕澂先生对应上述三种缘起说,分析了不同的缘起说所对应的实相说。他认为,与业感缘起说对应的实相说是“四谛”说,即根据众生的现实感受,依层次追究其苦集灭道四种真实;与受用缘起说对应的实相说是“二谛”说,即真理所适用涉及的范围,区分为世俗谛和胜义谛两种真实;与分别自性缘起说对应的实相说是“三谛”说,即通常唯识学所讲的“三性说”,即根据众生对诸法自性的认识完善与否,区分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种真实。尽管由不同的缘起说所显示的诸法实相的名称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业感缘起将四谛归结为“灭谛”之完全清净的实现,受用缘起将二谛的最终归宿落实于“胜义谛”上,自性缘起将三性的最终判别标准置于“圆成实性”之中,可见,“在这些真实中间仍旧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它们都用人生的究竟一个目标来作判断”。“这些无一不是人生的究竟处,也就从这上面看,合拢它们来才是一个全体的实相。”[32]吕澂先生从实相的角度,融通了各派佛学的要义,突出体现了佛法的“一味”之精神。
其中,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业感缘起说可说是整个佛法缘起系统中最为基础的、具体针对人生苦迫之根源探索的缘起说,因此,我们在探讨缘起学说时,理当以业感缘起说为重点和出发点。“业感”一词,本为玄奘大师在译经时所用的特殊译语。如所译《俱舍论》说:“如上所论十六地狱,一切有情增上业感。”[33]特别在唯识系论书中,玄奘大师大量采用“业感”一词。吕澂先生指出:“业感缘起是就当前的人生现象,依着逻辑的次序分析为十二部分(从‘无明’到‘老死’)来立说的。这十二部分也称做‘十二有支’,它们的相互间是以‘缘起’的关系,构成一系列的因果。以缘起说因果,可看做佛家解释因果规律的一个特点。”[34]在阐述业感缘起说特点的同时,吕澂先生发前人之未覆,揭示了业感说所体现的佛法对于人生的现实关注,特别是以自感、共感、类感的分类法,从自身的业感,拓展到众生共业之感,以及众生的相续之感。吕澂先生的这一分法,即清除了在“业感”问题上的狭隘、单一、片面的理解之风气,荡涤了笼罩在业感问题上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而且,赋予业感缘起说以更为宽泛的解释天地,从个体、局部,向群体和全局拓展。佛陀有言,缘起甚深。其精深的内涵在于引导众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把握其相互间切实的关系。并由此发现,在业感缘起的学说中,已经孕育了受用缘起的主客观的结合的思想——共感,以及自性缘起说的结合宇宙人生综合作用的思想——共感与类感。因此,由业感缘起说向受用缘起说及自性缘起说的发展,是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的,也是缘起说深藏隐含的甚深意义不断为佛子所理解、显发、阐述的过程。
根据吕先生的阐述,可以将佛法的缘起说归纳为下表:
名称 业感缘起说 受用缘起说 自性缘起说
特点 注重业力作用 注重主客观的结合 注重整个宇宙人生的贯通
实相内容 苦集灭道四谛说 胜义世俗二谛说 遍计依他圆成三性说
所证实相 灭谛 胜义谛 圆成实性
主要内容 十二支缘起 蕴处界三科 五位百法
涵盖范围 有情世间 器有情五蕴三世间 涵盖一切法之法界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吕澂先生特别注重缘起说与实相说结合,对业感缘起、受用缘起、自性缘起说予以全面的把握,并由此描绘了佛学缘起理论的完整体系。缘起与实相两体系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过旷日持久的争辩,但是,从学术的流变历史考察,缘起说与实相说仅是学术视角的不同,而其作为佛法的宗教意义却是一致的,缘起说是实相说的基础,实相说是缘起说的必然结论。丧失缘起说的实相说是无根基的梦呓之想,而无实相说之归宿的缘起说仅是名想的架构、学术的游戏,为龙树菩萨所斥的“戏论”,无任何实际的人生关怀意义和宗教的终极关怀价值。因此,学佛者当深悟缘起的深意,并借此缘起说厘清实相,真正为行持悟入实相准备好信解的道粮。所以,吕澂先生在对三种缘起理论详细阐述之后,于本文的最后指出:“综合以上所说三种缘起,从业感到分别自性,也就是从个人生存的体验到全体人生的变革,可说是大致包括了所有对象的缘起法则。又对于实相的认识从部分的苦集到全体的圆成,也可说是范围广阔了。在它们中间始终贯穿着实践的、变革的意义,而这一转变的关键又都见得出在于人生向上的自觉,这是应该特加注意的。”[35]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吕澂先生的学术探究中,他特别重视缘起说乃至整个佛学体系对于人生实际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变革人生的重要意义。这是需现世学佛者所切记把握的。
佛法本是释尊觉世之三业大用的载体,并非学者书斋中的玩赏品,更非商家蛊惑人心的推销品,而是关涉人生的根本真理,其实践性和现实的关照性是其主要特征。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佛法在行持上的实践性及在现世当下的关照性,都是对于佛法生命力的摧残和扼杀。由此,我们可以从吕澂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发现一个学者对于佛陀甚深教法在现世的重要人生指导意义的关注。
三、观行但愿笃实,转依贵在行持
《观行与转依》一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佛学》杂志1954年第七期上,是吕澂先生关于佛学基本问题的论题之三。《观行与转依》一文论述佛法行持的基本观法和戒定慧三学,并阐述了观行之结果,也即唯识学所谓的“转依”——即解脱,对佛法实践观的具体内涵作了精到的分析。本文开宗明义,确认本文系探讨佛法实践之原则性问题,说明本文与前述的二文,构成完整的体系,是佛法基本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正觉而出离的宗旨出发,经过缘起与实相的基本教义体系的阐述,最后归结为对实践性的观行的关注,吕澂先生完成了对佛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观行,一般而言,是指观心之行法。即观心修行,鉴照自心、明了本性。或指观法之行相。佛经有言:“若不解大乘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义谛:习种性、长养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性,其中多少观行,出入十禅支,一切行法,一一不得此法中意。”[36]由此可见,观行在佛法中不仅重要,且是以对大乘佛法经律的“胜解”为前提的。佛法有言,学佛的过程当遵循信解行证之次第循序而进。所以,观行的重要性尤显突出。吕澂先生指出:“实践的总内容,可以‘观行与转依’一命题概括了它。佛家实践全程所经的各阶段,都和智慧分不开来。像它开始的‘胜解’,相继的‘加行’,一概由智慧来指导、推进,乃至最后究竟的‘正觉’也以智慧的圆满为标准。还有,佛学看做行为规范的‘八正道’即以对于实相的正确知解(即‘正见’)发端,而推广到‘四摄’‘六度’也以高度的智慧(即‘般若’)为终极。这样由智慧构成的见解所谓‘观’,便始终和‘行’联系着,并称为‘观行’。观行的效果在于内而身心,外而事象(在认识上作为对象的事物),从烦恼的杂染趋向离垢的纯净,又从知见的偏蔽趋向悟解的圆明,随着观行开展,提高程度,终至本质上澈底转变,这便是‘转依’,它又是和观行密切相关的。所以,现在说‘观行与转依’,便可概括了佛家实践的全体内容。”[37]观与行,以及观行与转依的关系,以及次第辗转的程序,在此已经表述清楚。
在佛法中,观行始终与智慧相联系,为佛陀对众生的具体的“观慧”之开示。但是,佛陀在其一生的弘法生涯中,密切联系当时印度社会的实际,洞察众生的根机,适时应机地指导众生的观行。从最初的“八正道”开始,即:正见——正确的知见,正思惟——正确的思考,正语——正当的言语,正业——正当的行为,正命——正当的职业,正精进——正当的努力,正念——正确的观念,正定——正确的禅定。这一内容特别针对印度社会所存在的、并在佛陀时代成为风尚的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两种极端性倾向。又拓宽为内容更为丰富的“三十七道品”,这是以人生为立足点,观照世间的正确的思心所活动。其内容除上述的八正道外,还有:一、四念处,又作四念住:(1)身念处,即观此色身皆是不净。(2)受念处,观苦乐等感受悉皆是苦。(3)心念处,观此识心念念生灭,更无常住。(4)法念处,观诸法因缘生,无自主自在之性,是为诸法无我。二、四正勤,又作四正断:(1)已生恶令永断。(2)未生恶令不生。(3)未生善令生。(4)已生善令增长。三、四如意足,又作四神足。(1)欲如意足,希慕所修之法能如愿满足。(2)精进如意足,于所修之法,专注一心,无有间杂,而能如愿满足。(3)念如意足,于所修之法,记忆不忘,如愿满足。(4)思惟如意足,心思所修之法,不令忘失,如愿满足。四、五根:根为能生之意,此五者能生一切善法。(1)信根,笃信正道及助道法,则能生出一切无漏禅定解脱。(2)精进根,修于正法,无间无杂。(3)念根,乃于正法记忆不忘。(4)定根,摄心不散,一心寂定,是为定根。(5)慧根,对于诸法观照明了,是为慧根。五、五力:力为能破恶成善之力用。(1)信力,信根增长,能破诸疑惑。(2)精进力,精进根增长,能破身心懈怠。(3)念力,念根增长,能破诸邪念,成就出世正念功德。(4)定力,定根增长,能破诸乱想,发诸禅定。(5)慧力,慧根增长,能遮止三界见思之惑。六、七觉分,又作七觉支或七觉意:(1)择法觉分,能拣择诸法之真伪。(2)精进觉分,修诸道法,无有间杂。(3)喜觉分,契悟真法,心得欢喜。(4)除觉分,能断除诸见烦恼。(5)舍觉分,能舍离所见念着之境。(6)定觉分,能觉了所发之禅定。(7)念觉分,能思惟所修之道法。此七科三十七道品,基本上涵盖了声闻乘佛法的观行,其内容之具体详尽,充分体现了原始佛法“笃实”严谨的风范。
而吕澂先生在本文中则是以大乘中观学派之“空观”和瑜伽行派的“唯识观”为其阐述的重点。无论是中观学派,还是瑜伽行派,作为大乘佛法的倡导者,他们的观行都是以“四摄”“六度”为其宗旨的,所以,无论是菩萨投众生之情,善巧摄引,以令度脱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四摄法,还是大乘佛教中菩萨欲成佛道所实践的六度法,均具有强烈的对治悉檀和为人悉檀的倾向,但是,其中的般若波罗蜜,则具有第一义悉檀旨趣,能够通过其引导众生观悟行证诸法实相。由大乘佛法的教义出发,观行两者,可在以“般若慧”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解深密经》将此六波罗蜜摄为戒、定、慧三学,其中施、戒、忍三波罗蜜为增上戒学所摄,禅波罗蜜为增上心学所摄,般若波罗蜜为增上慧学所摄,精进波罗蜜则通为三学所摄。而瑜伽行派再将般若波罗蜜展开为方便善巧、愿、力、智等四波罗蜜,合为十波罗蜜,作为菩萨之胜行,以配菩萨十地,说明修行次第。大乘中观学派的“空观”与瑜伽行派的“唯识观”,都是在三学四摄六度的基本前提下所构建的。只是大乘中观学派侧重于有情的认识方法,瑜伽学派侧重于有情的认识过程;中观学派侧重于直接探究诸法的实相,瑜伽学派侧重于探究诸法事相认识的层次。
中观学派以龙树、提婆菩萨为其发轫者。中观学派的思想体系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八不中道的缘起观,龙树菩萨在《中论》之首,即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阐述缘起观,揭示了宇宙万法皆由因缘聚散而生灭,实则并无生灭实相之理,故名“中道”;其次是以“三是偈”所揭示的三谛圆融观,故亦称“三谛偈”,即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之偈颂。此颂揭示,世间一切现象,均由各种因缘条件产生,并无固有自性,人们所见所闻实在事物,皆为施设之名想概念,自性则空无所有,与《大智度论》卷三十一所讲的“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是名性空”的“性空”说,及《大乘义章》卷一所谓“诸法无名,假与施名,故曰假名”,“废名论法,法如幻化,非有非无,亦非非有,亦非非无,……以名呼法,法随名转,方有种种诸法差别,假名故有,是故诸法说为假名”的假名说共同组成了中道体系;最后为实相涅槃之成就观,即《中论·观涅槃品》中所谓“分别推求诸法,有亦无,无亦无,有无亦无,非有非无亦无,是名诸法实相,亦名如来法性,实际涅槃”,认为世间诸法之实相即是毕竟空,无生无灭,涅槃寂静,故世间与涅槃相互之间并无区别,此说成为大乘佛教得以世俗化的方便阶梯。中观学派认为,掌握以上诸要义后,便能破除一切错误无益之“戏论”,此即《中论·观因缘品》所说的“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包括由贪引发的“爱”,及对事物固执的“见”,特别是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见解。因为世俗的名想概念所获得的认识,都包含在戏论范围之内,也即所谓“俗谛”。而依佛理而直觉的现观,能证得诸法实相,为“真谛”。中观学派的这些思想,成为我国佛教之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开宗立派的重要依据。
吕澂先生认为,中观学由“不二”法门入手,消解世俗的偏见;由“八不”的否定方式,对生灭、一异、常断、来去等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众生在理解上的矛盾性,逐个加以破除,显发诸法实相。他对中观学派的学术特点有着十分精到的归纳:“佛家的中观是辨证的,因为它一方面能够如实地了解事象,而事象实际必然是辨证的开展,这就规定了中观的性质。另方面,中观的方法着重在把握思惟的辨证规律,而善巧地运用它,克服认识上的各种错误,这尤为构成中观辩证性的重要原因。”[38]既肯定事相辨证开展的实际,又充分展现思维方法即“观慧”上的辨证性。故吕澂先生郑重指出:“中观的辨证性是出于思惟和实践上的要求,不容不尔,可以无疑。”[39]
而由无著世亲菩萨所创立的瑜伽学派,其所建立的唯识观,认为一切外在的现象都仅仅是心识的变现,并非实存于外。《唯识二十论》说:“安立大乘三界唯识,以契经说三界唯心,心意识了名之差别,此中说心意兼心所,唯遮外境不遣相应。内识生时似外境现,如有眩翳见发蝇等,此中都无少分实义。”[40]《成唯识论》卷七说:“云何应知,依识所变,假说我法,非别实有,由斯一切唯有识耶。颂曰: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论曰: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转变名。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唯言为遮离识实物,非不离识心所法等。”[41]这是指由诸识自体转变为分别的见分、所分别的相分,脱离此诸识所变之能取所取,则无任何实我实法,故说一切皆唯识。这即唯识之含义。吕澂先生断言,无著世亲的唯识观是在龙树中观学基础上的发展。他指出:“无著学系,发展了这样的中观,加以概念认识和实践行为的辨证的统一,更丰富了它的意义。他们区别概念为世俗的(只是世人所公认的),和世俗谛的(并且与实相相随顺的),性质各各不同,所以要拣择运用,配合着克服烦恼和偏见,逐渐达到圆满的认识,同时也净化了行为,这样就有种种真实义,像‘世间极成’”的、‘道理极成’的、‘烦恼障净智所行’的、‘所知障净智所行’的等等,自成一类中观境界。最后,他们更用‘唯识观’为方便来贯通这一切;藉‘唯识’一概念,扫除了各种偏执,再一转折构成完全的中观。”[42]
唯识与中观的修行实践,则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法统一戒定慧三学,将戒定归于慧学的特点。吕澂先生在分析了小乘戒成就自身清凉、大乘戒联系自他全体的不同特色之后,深刻指出:“人们对于人生实践的真知灼见,决非由少数人的悟解便能获得完全,而必须依赖大众智慧的积累,所以虚心地向他人吸取经验,逐渐扩充,逐渐深厚,才会达到完全的地步。”[43]由此断定大乘佛法的戒学之意义在于使众生的行持,在相互增上的氛围中臻于完善。
同样的,大乘佛法和声闻乘佛法在定学上也意趣相左。声闻乘佛法注重“入定”的形式和程式,如最早流传中国的安世高所倡导的“数息法”,即为防止心思散乱,逐渐消除寻思,助人进入定境的方法。但是,大乘佛法将定学的意义予以极大的扩展,不拘泥于动静,不滞粘于形式,不局限于程式,而是以是否契入诸法实相为其定学的最高判断标准。所以,中国以禅宗为代表的禅学倡导不拘动静,而以思心所随顺实相为其修学之要,即以大乘佛法的定学为依据。在大乘佛法中,无论是规范日常之行为的戒,还是沉静思虑的定,都是以离不当分别者,断不当行持者为其目的,其最终的效用还是当如禅宗所揭示的,以般若为禅,即将戒定之行持归到慧之观。这才是全面的、完整的、灵活的、实际的观行。当然,其观行的最终结果在于解脱的出离,即大乘瑜伽行派所深究的“转依”。
吕澂先生指出:转依是观行的结果。“这个范畴是在佛学发展的盛期即无著的时代,才用来替代‘解脱’的。它更能积极地表示解脱的本质,并说明如何由基本上解决问题。在此以前,佛家注意到定的功效,可以抑制或消灭下地或下一级的烦恼,而生起或增长上地或上一级比较安静的心思,以为这在身心的负担上减轻了粗重感觉而增加了轻安感觉,‘依止’转变,就称那样的状态为‘转依’。但到了无著引用这一范畴,意义便大有不同。它并不限于身心的转易,又还联系客观事象的变革。要是略加分析,在主观方面,这是注重认识的质变,而用名想或概念的认识来做关键的。名想认识和行为本可有相应的关系,某些名想认识常连带着为某种行为的准备或助力,所以行为的错误常常缘于认识的错误,而改变了认识也会间接改变了行为。至于一切名想认识相互间的联系,自成一种系统,又常依着各人生活环境而各有其类型和特点。这在心理方面的基础,可以从它们存在的依止处──佛家所谓之‘藏识’──去了解。因此,只要藏识上名想习气的染净种类互有消长,自然发生粗重或轻安的不同感受。而由于人生正向是从染趋净的,其间逐渐转变,终至染尽净满,身心面貌突然改观,这样说为‘转依’。至于客观事象的一面,不是简单地从名想认识的转移便直接有了改变,却是由认识的不断矫正,事象实相的显现益加了然,这再引起行动,革新事象,使它更和实相随顺地发展。所以,在认识和行为的联系中,主客两面平行的前进,而真正的转依即是由这样的途径完成的。”[44]在此,吕澂先生表达了如下几层含义:首先,转依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揭示解脱之本质的名想概念,其所说明的不仅包括解脱的特点在于转识成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指明了解脱的基本途径和过程。此在唯识体系中的有详尽的分析。转依具体而言,即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的“八识四智”之转依的内容,以及转依的最终完成——法界体性智的实现过程;其次,转依的概念虽由无著菩萨赋予解脱之含义,但其名称的由来却源于定学,其原义是由定而产生的轻安可以成为修学者依止处,并引身心由粗重之烦恼所缚中转移出来;再次,无著菩萨运用此转依的名想概念,在于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主观上认识的质变,即藏识的由染转净,终至染尽净满。客观上事象的实相显现,即引发实际的人生行持的变革。主客观的相互消长,事相矫正认识,认识推动事相,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推动转依的完成,即八识转成四智。最后,吕澂先生在此隐含了一层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未明确阐明,即转依并非如叙述的次第一样,需待观行的圆满方才开始,而是包含在观行过程中,观行的完成固然是转依——即解脱,而观行过程的本身就是转依过程。转依对于解脱意义的拓宽,主要表现在解脱本身仅是结果性的,而转依不仅是结果,而且是过程本身。
佛法是实践的宗教,是注重终极关怀的普世教法。因此,在佛法中,修行的实践可以说是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了修行而奢谈佛法,无疑是空中楼阁。需要指出的是,佛法的修学者,需要笃实的观行,而由行持才能达到转依的目的,转依决非故弄玄虚,而是需要以持久不懈的行持为基石的。转依的实现是达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境界。但教界末流虽高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强调自性即佛,拜佛即拜己,固然动人悦耳,似乎也契合究竟法门。但无论事相或理论,如无前提条件的限定,推向绝对则必将走向其反面。高调的深层,既失去自性,也无处寻觅佛陀;就如“不度己身先度生”、“不为自己得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等,动人的口号背后,是凡夫我慢心的高扬,一切世俗的东西以合法如理的面目出现,成魔之人与成佛之人难以分清。佛出于不可思议愿力而成就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并不天然抹平众生与佛陀之间的实际距离。其原因在于,佛陀早已给我们明示:凡夫在苦、惑、业中翻滚,世俗的各种束缚使众生难于接近他。佛法强调修证,就在于强调须打破难以打破的束缚,以接近佛陀,而这是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近的。
基于教界颟顸佛法的事实,吕澂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著述了《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等三篇旨在阐述佛法基本问题、显发佛陀真意的论文。今天学佛者读来,当有诸多收益。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吕澂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光照华夏,已是中华汉语系佛教不容忽视的宝贵学术财富。综合考察,吕澂先生的佛学思想被学界称誉为三藏兼备、五明俱通,决非溢美之词。其学术地位和成就可由下列几方面衡量:
首先,对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所盛行的佛学研究法,亦即以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各类学术方法去研究佛教,吕澂先生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将这种研究方法及学术态度介绍到中国佛学界,并且身体力行,成就博大。可以说,吕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其次,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不仅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博。从其著作分类,他在佛教经典的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藏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等方面无不融会贯通,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综合衡量,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他都堪称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第一人;再次,在学术创见方面,多项学术发现之外,吕澂先生的大部份论文,都有创见之功,其独步学界及佛坛的学术洞察力可谓敏锐深邃。总之,吕澂先生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材培养,以及佛经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学术遗产,值得中国佛学界珍惜、珍视!